陶渊明,始家宜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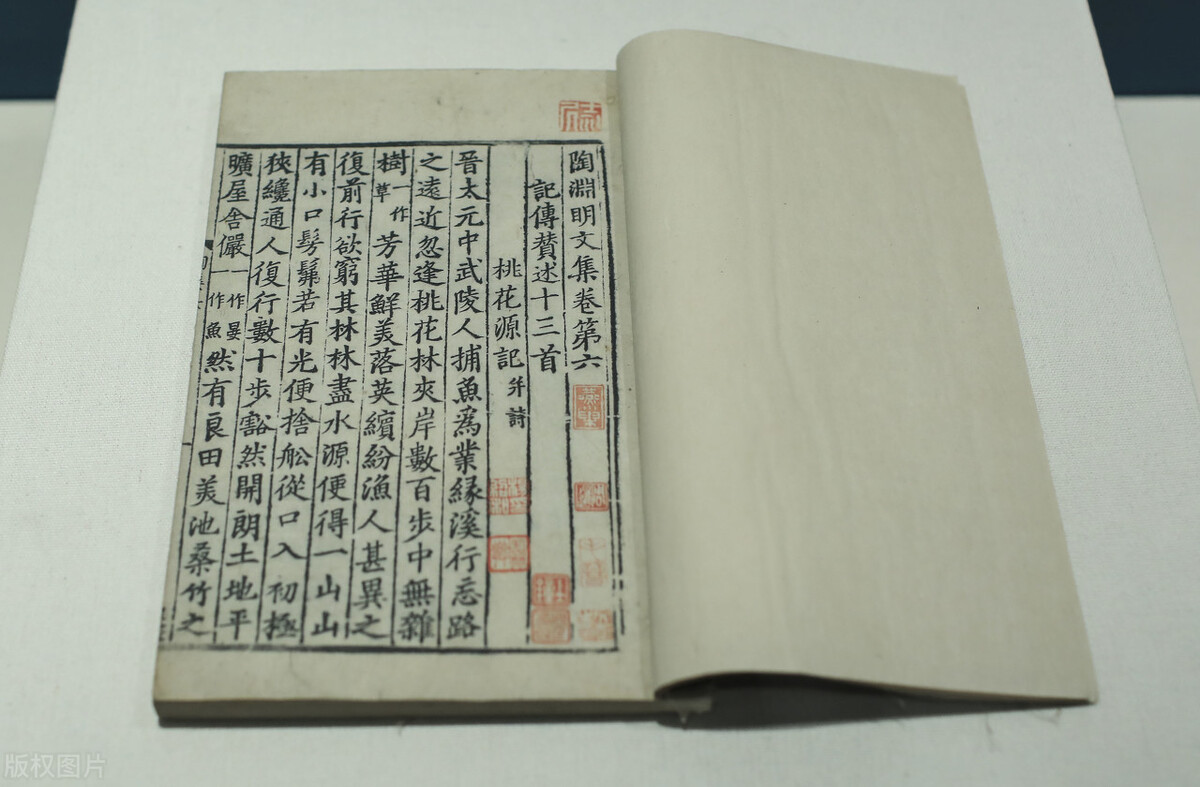 陶渊明,始家宜丰 鄢文龙 胡伏坤  “陶渊明故里何在”的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也”。 作为宜春人,我更倾向于陶渊明始家宜丰。 通过多年考察与研究,这里拟从史传中所冠身世之地名、陶侃之里籍、柴桑故里、田园居、旧居、上京等概念的理解与实证进行理性分析,特别注意从陶渊明自身及其文本寻求内证,说明陶渊明确实“始家宜丰”。 陶渊明父母曾经在宜丰这个地方居住过,陶渊明有“入仕”前在宜丰居住的经历,并有一段“晚年回归”宜丰的历史。  一、史传冠以身世之地名,不足为故里之证 众所周知,史传冠在传主姓名前面的地名,和补在传主后面的地名,通常指传主姓氏之郡望,且大多为“郡”一级之地。或是传主姓氏之发祥地,或为该姓中最出名先祖之“封地”,并不指传主具体之籍贯、故里或者故乡。 因此,根据史传所标传主之出身地名认定该地是其故里,往往容易形成错案。事实上,历来研究陶渊明者,根据沈约所载认定陶渊明故里就在柴桑的说法,已经众说纷纭。这样的理解,势必造成三种错失: 1.掩盖了东晋时期的历史真相 认定陶侃为“柴桑人”者,所依主要是《晋书·陶侃传》载“吴平,(陶侃)徙家庐江之浔阳”。其所论把“庐江之浔阳”衍生成了“浔阳之柴桑”,完全属于张冠李戴,搞乱了东晋时的历史真相。事实上,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人口迁徙频繁,郡县关系非常杂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浔阳与柴桑原本均为县,前者属庐江(安徽安庆)管辖,在江北;后者在江南。到东晋初,浔阳为郡,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后来才迁往江南柴桑,其时在晋咸和(326——334年)中。也就是说,浔阳县与柴桑县重合在一起的时间,应当在330年左右。而330年,陶侃已经年届七十; 334年,则是陶侃死去的年份。因此,陶侃在“吴平”时“徙家庐江之浔阳”之“浔阳”,当为江北之浔阳,与江南之柴桑根本无关。因此,“陶侃为柴桑人”一说,不成立。 2.搅乱了“柴桑人”们自己的阵脚 所谓故里,通常是指父母的休养生息之地。至今为止,认定“陶渊明故乡在柴桑”的研究者,一直未能列举出陶渊明其父在柴桑居家的直接史证,甚至连可证明其祖曾经在柴桑居住过的间接史料,也未找到。基本上还是沈约的那句现话。最多有人把清代王谟在《江西考古录》里所说“陶渊明一生行止始终不离柴桑”搬以为证。其实,如今古柴桑境内争夺“渊明故里”的地方涉及九江、星子、武宁、德安四县,即使九江一个县内也有好几个地方在纠缠不清。这种看似“百花齐放”的乱象恰恰证明:人们在柴桑境内是不可能找到诗人故里的。 3.迷惑了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顺解 自古以来,用“陶渊明是柴桑人”一说去解读陶渊明的传略与诗文,不仅将一个胸怀大志却与世不容的诗人说成了一个生来性爱山水、厌恶官场又抨击时政的隐士,更彻底颠覆了陶渊明的本来面目,且留下了许许多多困惑与疑团。由此可见,根据沈约记载,认定陶渊明为柴桑人的说法,于史于理于情都捉襟见肘。 要真正弄清陶渊明究竟是哪里人,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回归到有关历史资料中去,弄清历史的真相。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从陶渊明自己所写的诗文中寻找“内证”。 二、以陶侃的里籍不足以论证陶渊明的里籍 现在,有研究者为了说明柴桑是陶渊明故里,既言之凿凿陶侃为“柴桑人”,也津津乐道九江某地有“牛眠地”和“鹤问乡”,甚至说陶侃父母就葬在这两地,也有专家频繁地考证,并下结论说这里就是陶渊明的故乡。如果只凭这两个材料,就完全可以断定“陶侃为柴桑人”,那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关传略里记载的“牛眠地”与两个“吊客”化鹤而去,无论它们是实际故事被神化,还是子虚乌有的传说,都不可能发生在如今九江地区。 1.陶侃老家非柴桑,柴桑无“牛眠地”与“鹤问乡” 《晋书·陶侃传》记载,陶渊明的先祖陶侃“本鄱阳人也”,是东吴“扬武将军”陶丹的儿子,“早孤贫”。“吴平”,“徙家庐江浔阳”;不久,他在两晋之交的动乱中发迹,曾为“江夏太守”,不久被封为“柴桑侯”,后被东晋王朝封为“长沙公” ;此后,便“移镇武昌”,一直在其“长沙公”的封地活动,最终老死于此。 依据这一史料史料,结合其它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由于陶侃的生卒年代是公元259年——334年,西晋开元的年份是266年,东吴灭亡的时间是280年。这就表明,陶侃在“徙家庐江浔阳”时已经31周岁,其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鄱阳”度过,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浔阳人”,更不能引申为“柴桑人”。 第二,《陶侃传》里明确记载“侃早孤贫”,陶侃本人咸和七年(332年)上表逊位时也对皇帝说过“臣少长孤寒”,也就是幼年丧父,非常贫苦。该《传》还载有一个陶侃母亲“截发易酒”招待鄱阳县令范逵的故事。这就告诉我们,他在鄱阳时已经没有了父亲,他的父亲也应当是死在鄱阳葬在鄱阳,不可能葬在柴桑。因此,柴桑境内不可能有所谓的“牛眠地”。当然,在陶侃后来被封为柴桑侯以后,陶侃有可能将其父亲改葬柴桑。但是,史料并无记载。 第三,《陶侃传》还载,陶侃在“江夏太守”任上“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后以母丧去职”,才发生“二客来吊”化鹤而去的故事。这又告诉我们,陶侃的母亲是死在“江夏”的“官舍”。众所周知,江夏在如今的武汉与黄石之间,与古柴桑相去甚远,而且陶侃任江夏太守的时尚未封柴桑侯,柴桑又非其故里,柴桑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什么“鹤问”的地名。 2.陶侃封“长沙公”之后,柴桑已非陶氏之故土 《晋书·陶侃传》载,陶侃是因平杜弢之乱而被封柴桑侯的。这,或许就是天下陶姓以“浔阳”为郡望的来由。但有二个史实不容忽视,一是《晋书·周昉传》载,与陶侃为儿女亲家的周访也曾被封为“柴桑县侯”,也是因为平定杜弢之功而被封的。两人因为同一个原因被封赠同一个地方,这本身就反映出乱世封赠的乱象,很难名副其实。二是陶侃在不久后被封“长沙公”,“移镇武昌”。这就表明,即使其家人曾在柴桑居住过一段时期,也会因改封而搬出柴桑。 因为,自古以来,“封妻荫子”乃所有铁血男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谁一旦梦想成真,在他的家族内,肯定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既然朝廷给了陶侃“长沙公”这种比“柴桑侯”地位更高的封赠,他的家人和后代就毫无疑问要追随发迹者到其最高封地去享受浩荡皇恩的。因此,无论陶侃是不是柴桑人,他的后代都肯定会在其封地居住。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晋书·陶侃传》有陶侃死后“葬国南二十里”、“立碑于武昌(今鄂州)西”的记载中找到佐证,而且还可在陶侃临终前一年给晋成帝的一个“奏折”中找到直接证据。陶侃在那个奏折中表示:自己深受皇恩眷顾,打算“归骨国土”,死后也要在封地继续效忠朝廷;并说由于“父母旧葬”“缘存处亡,无心分违”,最近“已勒国臣”“修迁”,准备亲自“奉迎”遗骨,一旦事毕之后就“告老下藩”。这表明,陶侃本人健在时,不仅举家迁移到了朝廷赐给的“长沙公”封地,而且连其父母之墓也“修迁”到自己的领地。 依据中华传统文化,古代社会,人死后是要回归故土的。陶侃既然把父母坟墓都改迁到了自己的封地,那就说明在陶侃心目中只有封地才是故土。祖坟是需要后人看守的。陶侃修迁父母坟墓的举动,不仅说明他的后代已经居住在他的“国土”,而且说明他的原有故居连看守祖坟的后代都不需要留守了。也就是说,柴桑那个曾经的封地内,顶多只会有一些陶侃的旁系子孙在那里居住,而不可能是陶侃嫡出后代的聚居地。这,或许就是一些论家以为陶渊明并非陶侃嫡系的潜在理由。 此外,各种晋史的《陶侃传》还一致记载,陶侃的“长沙公”封爵贯穿于东晋始终,一直到刘裕代晋以后才被降格为“吴昌侯”,由此可推他后代居封地而不居柴桑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以上分析表明,若就陶侃本人的履历而言,**,他不是柴桑人而“本鄱阳人”。第二,他在鄱阳时就死了父亲,所谓“牛眠地”的传说不可能发生在柴桑。第三,柴桑仅仅是陶侃生平中封侯拜将的重要驿站,不是他最终的归宿。因此,持“柴桑人”说的人们把“陶侃为柴桑人,他的后代也为柴桑人”作为论证陶渊明故里的依据,不足为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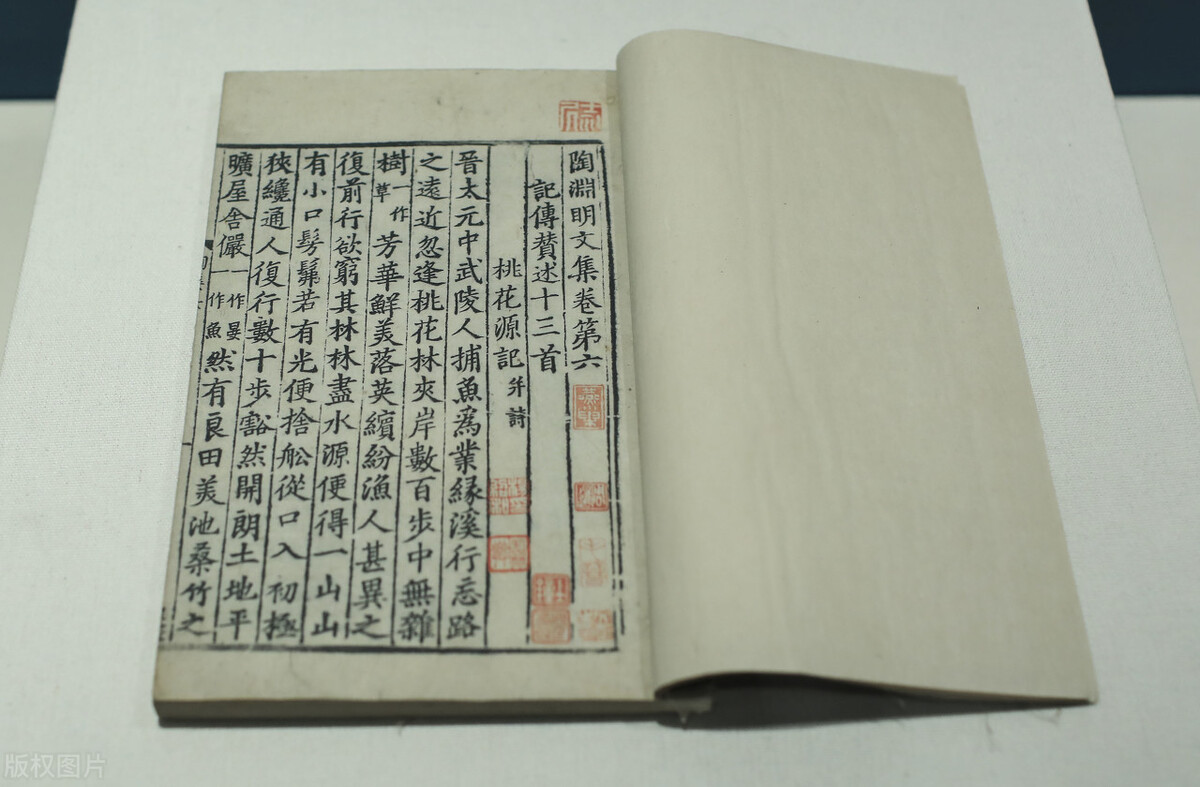 三、史载表明,陶渊明祖、父不居柴桑,柴桑非其故里 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例外出现。在陶侃有封地的前提下,其后代居柴桑或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陶侃死后家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内乱,在他的儿子们为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时,可能会有人“避乱”回柴桑。但这种可能并没有发生在陶渊明的家庭身上。 1.陶渊明之内外祖父均为武昌人 《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是“武昌太守”,领地在今湖北鄂城。陶渊明自己所写的《故晋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还说,其生母是“武昌名士”孟嘉的第四个女儿。这就告诉人们,在陶渊明的直系祖先籍贯中,无论内外,只与武昌有关,而与柴桑没有任何关系。 2.陶渊明之父亦无居住柴桑之迹 虽然陶渊明的父亲不见于任何正史,但几乎天下所有的陶氏家谱都认定他做过安城太守,领地在今江西安福。陶渊明自己也说过其父亲曾经“寄迹风云”(见陶诗《命子》)。风云者,官场也。史证谱载其父亲做过官的史实不假。这是陶渊明父辈不在柴桑居住的直接证据。 3.行止证实,陶渊明37岁前家不在柴桑 陶传与陶诗所折射出来的陶渊明的行止表明,他在37岁以前的“家”根本就不在柴桑。 首先,陶渊明29岁“起为江州祭酒”,任职地并非柴桑。所谓“江州”,应是东晋时成立的新州名字,它由原属扬州的浔阳郡和原属荆州的武昌郡组成。其州治设在武昌,后来才迁浔阳。所谓“祭酒”,应当是《晋书·庾亮传》所载庾亮在“武昌”首设的学官名称,与陶渊明《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讲的孟嘉首任庾亮所设学官是同一回事。如果我们把“祖茂,武昌太守”、孟嘉首任江州祭酒和陶渊明“起为江州祭酒”连接起来,既可顺理成章,也可说明陶渊明的家庭居址从其祖起就一直围绕着“武昌”在官场打转,只同陶侃的封地和势力范围发生关系。 其次,陶渊明在33岁之后做了6年桓玄的参军,其家也不在柴桑。陶诗《庚子岁五月为建威参军使都还》中的“建威将军”,指的就是桓玄,他是“南郡公”桓温的儿子,比陶渊明小4岁。庚子岁为公元440年。该年,袭父爵的桓玄已成镇守在江陵的“都八州军事”。陶渊明替桓玄出使京都,说明他在桓玄那里的地位很高,也说明他当时肯定要追随在桓玄左右,不可能把家安顿在别的什么地方。同时,我们通过查阅其它史料还可得知,桓玄的父亲桓温年轻时曾经受陶侃节制、同庾亮交好、收孟嘉为臣,是维系东晋存在的重要将领,支配司马王朝有数十年之久。这其中所隐现的种种关系,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陶渊明投靠桓玄的缘由,也可以佐证陶渊明家祖孙几代的行止都与江陵、武昌发生关系,很难从中找到他家居柴桑的蛛丝马迹。 再次,陶渊明自己说他37岁时的家在“江陵”。如果说《庚子岁五月为建威参军使都还》还没有讲明他“还”哪里,那《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则直白无遗地道出了他的家居所在就是江陵。“辛丑岁”为公元401年,诗人37岁,仍在桓玄部下当参军。从《晋书·桓玄传》可知,该年桓玄镇守襄阳,正挥师向长江中下游推进,与朝廷抢夺长江中下游地盘,以逼近京师,为日后造反图谋。因此,诗人“庚子岁”的“使都还”,是“还”桓玄军中;而“辛丑岁”的“还江陵”,则是从柴桑出发还“家里”,原因是“赴假”。 “赴假”是“奔丧”的同义。“奔”谁之“丧”呢?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有“弱冠逢世阻”语以及各传讲他少年丧父可知,这次应是奔其母亲之丧。诗人要离开桓玄军中到江陵去奔母丧,本身说明诗人当时的家居在江陵。诗人的《祭程氏妹》,也有“昔在江陵,重罹天罚”的诗句,可以佐证这个“赴假”就是到江陵去奔其“天罚”。 这些由陶渊明亲口说出来的史料表明,到诗人37岁的时候,其家居江陵。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从陶渊明祖父起到他本人37岁左右止,未见史料说明其“家”柴桑。显然,一个祖辈与父辈都无在柴桑居住记载者,我们很难说其故里在“柴桑”。 4.陶渊明文本有柴桑非其老家之确证 从逻辑上讲,诗人37岁前的家不在柴桑,并不等于他在37岁以前就没有在柴桑居住过。因此,仅凭上述文字中说“陶渊明祖孙几代行止都与江陵、武昌发生关系,很难从中找到他家居柴桑的蛛丝马迹”,还不能完全断定其父母之邦不在柴桑。能够作出这种断定的,应当而且只能是陶渊明自己的相关自述,这就是陶渊明亲口所说的老家:“园田居”。 陶渊明有一组《归园田居五首》的组诗。其一中的“一去三十年”与其四中的“一世异朝市”表明,诗人是在离别三十年后回到“园田居”来的,年纪当在50岁开外。特别是这组诗的其四有“试携子侄辈”、“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朽残株”的叙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带着子侄在坟山上转来转去寻找先人坟墓”的图画。正是由于诗人看到坟墓年久失修,只剩洞穴(井)与罗帷(灶),连上面的植物也轮回过许多次的破败景象,故而发出“一世异朝市”的感叹。 对这组诗词的正确解读应当而且只能是:从诗人有“弱冠逢世阻”(见陶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诗句以及“迟出”“早归”的说法,联系古人在父母死去必须守制三年以后才能外出谋仕的旧律,少年心怀高趣的诗人从20多岁外出到50多岁回园田居正好是三十年的样子。诗人的“一去三十年”,讲的就是从少年离别“园田居”到晚年回归“园田居”的时间间隔,而不是从“起为江州祭酒”到“彭泽辞令”的时间间隔。还有,在这个“园田居”的“昔人居”中,既有诗人20岁“弱冠逢世阻”故去的父亲,也应包括“我年二六”(陶诗《祭程氏妹》语)时早逝的那个“慈妣”。这种对“昔人居”所作的分析,能够把许多诗篇与史料连接起来通说。这种解读显然告诉我们,这个“园田居”不仅是陶渊明的故里,而且不在柴桑或其附近。 因为,陶渊明在41岁时做与辞的官职是彭泽令,这就可以断定他当时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都住在柴桑。自《周礼》施行以来,“孝”为人子之本,父母在生要朝夕侍奉、父母死后须按时祭奠,是所有人的必修功课。陶渊明“一去三十年”都不曾到过有着“先人居”的故乡这种现象,只能用“园田居”不在柴桑范围之内、不方便到达来说明理由。同时也能佐证陶渊明“弱冠逢世阻”前后的家根本不在柴桑。 面对这个“一去三十年”的“复得返自然”,立足于“柴桑人”说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即使是大师也会在此处“大跌眼镜”、动作失常。由于受“柴桑人说”的局限,他们在解释这组诗词时都把本指坟墓的“坵垅”说成田野,把坟墓构件的“井灶”说成水井和厨房,并无端将“一去三十年”改成“一去十三年”等,一错再错,给后人正确理解诗意带来误导。 误导之一,是把“一去三十年”改成“一去十三年”后,势必要将陶渊明原本“少怀高趣”、“世阻”“迟出”、官场得意又失意、归隐之后又不隐等丰富经历简化为“错入官场”与“归农求隐”两段,这就颠覆了诗人的生平。 误导之二,是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和“归园田居”合为一体,忽视他离开官场以后到“归园田居”之间还有“亭亭复一纪”的生平际遇和思想变化过程,因而对诗人在辞官以后所写的诗文发生误解或曲解,而这些诗文,恰恰是正确理解陶渊明思想的关键所在。 误导之三,是没有看清《归园田居》其四有诗人在园田居时上山祭拜父母坟墓的情形,把令作者心旷神怡的“园田居”描绘成惹人伤心的“废墟”,把诗人彼时久违故乡的心情衍生为对世事变化的感叹,把诗人在“园田居”时所产生的逃世思想拔高为对现实的批判。本来,诗人在那里所展现的,仅仅是看到已有“一世”时间没人祭拜的“昔人居”荒芜破败,哀叹自己的身世遭遇,并表白自己已从世事中解脱了出来。可是,经过有的大师的随意解释后,诗人与故乡揖别三十年的真实情感图画就演变成诗人愤世嫉俗的画面,诗人思想内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烙印也被演变成在诗人内心激荡的不满、反抗与斗争精神,其结果只能与陶渊明为隐士的定见形成悖论。 这些事实上存在已久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误导,本身就是对陶渊明柴桑人一说的否定。 因此,走入陶渊明的文本,如果要说陶渊明究竟是哪里人,其实他本人早就给过我们答案:我乃“园田居”人也。 如果说作出这一判断,只是一个孤证,那么,在陶渊明的其它许多自述晚年回归“园田居”的诗句中,就有一系列连环证据。特别是在《酬刘柴桑》、《与子俨等疏》、《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连雨独饮》、《还旧居》等十来篇诗作里,都或明或暗讲述了柴桑仅仅是他本人一度的暂居地,自己52岁归来的“园田居”那个地方,才是他真正的“故里”。 《酬刘柴桑》说“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显然是作者在柴桑这个地方对刘姓柴桑县令所讲的自己想法。所谓“远游”,无论怎么说,都是要带着老婆与幼子远离柴桑到别的地方去。从诗中有“嘉穟养南畴”一句以及《宋书 ·刘裕本纪》关于刘裕向晋安帝进献九穗粟米(嘉穗)的事件记载可知,诗人写这首诗词的时候不早于公元416年,即诗人52岁时的秋天。那时,正值司马休之在荆州叛乱,长江中游一带战事频仍,可见作者是不可能有什么闲情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的。再说,本诗中还有“穷居寡人用,时忘运四周”的自述,说明诗人当时连起码的生活资料也不足、每天只是打发日子,根本不具备旅游的资本。可见, “远游”,就是“远离游走之地”。若此意会,诗人要远离柴桑“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在诗人那里,柴桑只是自己的“游走之地”,他的远游,就是要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去过上原来那种田园般自由自在的生活。 《与子俨等疏》说“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这是诗人自述在“年过五十”之时写的,同《酬刘柴桑》应属同一时期的作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同《酬刘柴桑》连起来理解,将之视为诗人对为何“远游”的脚注。意即:怨恨自己辞去彭泽令以后住在柴桑没有“二仲”那样的知音,也不是真正像“老莱子”那样隐居江湖,使自己向往“二仲”“老莱”之心苦久煎熬,现在要不惜一切去追求原来那种既有知心又有闲趣的生活,即使希望渺茫也在所不惜。故此在临行前写下《与子俨等疏》,交代长子等一些注意事项,“启动远游”。这个意思十分清楚地表明,在诗人那里,柴桑只是没有知音与闲趣的暂居地,只有那个“缅怀在昔”的故里,才是他可以找到知音与闲趣之地。 《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诗人有“复得返自然”的感受。 这个“复得”,毫无疑问是“缅怀在昔”的实现,说明他已经回归故里“园田居”。 《拟古九首》,作者怀着“但恐人我欺”的心情,“已与家人辞”,带着“翩翩双飞燕”,“相将还旧居”,在询问“君情定何如”的时候,把自己东西游走的那段历史一一坦陈,既禀明自己在外没有学坏,又诉说辞官是迫不得已,还表白自己回来会彻底隐居,明显是向故里父老“汇报”“赔情”。这组诗词的存在,也反映出诗人的“旧居”不在柴桑。只有用“晚年回归园田居”去理解,才能“一通百顺”。 《饮酒二十首》说自己辞令后“亭亭复一纪”的日子是“栖栖失群鸟”、“夜夜声转悲”,好不容易才“达人解其会”、“飞鸟相与还”,得到了“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的生活,并从“悠然见南山”中悟出“心远”真意。 其中的“一纪”,是个非常准确的时间单位,长度为12年(中国人用12生肖纪年,一个轮回成“一纪”)。这就告诉我们,诗人真正“心远,”变成“达人”,是发生在辞官12年以后的事情。其中的“心远”,既是诗人在故里“虚室绝尘想”的结果,也是其晚年厌世思想的精髓。“亭亭复一纪”以后的“飞鸟相与还”,是带着老婆幼子回家乡。 过去,持“柴桑人说”的人说“一纪”指的是从“起为江州祭酒”到“彭泽辞令”,正好12年,根本没有考虑《饮酒二十首》之间的前后联系,事实上也无法把“栖栖失群鸟”、“夜夜声转悲”的思乡情意诠释清楚,更无法把握诗人产生“心远”思想的准确时间与整个过程,于是只好说什么诗人生来就性爱山水不爱当官,在官场非常痛苦云云,无异于用“先验论”霸权式地强解诗人。 《连雨独饮》说“故老赠余酒”,故里乡亲给了自己“饮酒”即心远尘世的机会,“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讲述刚刚回来(试酌)时抱定“心远”不理尘世百般事务,过了一段时间(复觞)以后连“天”(连雨)的存在也不记得了。 联系到“心远”一词出现的时间背景和公元419年天下久雨久旱的历史记载,这应当是诗人在“园田居”生活几年以后的“饮酒”状况:诗人“心远”已深,竟然麻木到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也无动于衷了,与原来那种“或大济于苍生”的抱负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上述诗篇,皆为诗人50多岁时所写,在内容上前后相承,互相照应。不仅再现了“园田居”的乡景乡情,而且还还原成一幅晚年回归故里的详细路线图,为我们通解诗人的生平和思想留下了十分清楚的线索。  四、“园田居”故里究竟何处,虽有争论,但持有定论 关于陶渊明的故里“园田居”在哪,我国史学界很早就关注并一直争论着,目前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园田居在柴桑,一种是园田居在宜丰。自唐以来,史学界对于前者是否认的,而对后者则予以认同。 1.增删有据,豁然开朗 从《晋书》删除“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也”的旧说,而增加“祖茂,武昌太守”的记载可以看出,这本身就是《晋书》编者对《宋书 ·隐逸传》的否定,也为“园田居”在何处的研究开辟了途径。 唐初,大文学家、唐朝宰相房玄龄等在编写《晋书· 陶潜传》时,没有沿袭沈约《宋书》、萧统《陶传》、李延寿父子《南史》的一致说法,在陶传中删除了“浔阳陶渊明”等字,直呼其名之后,还增补了“祖茂,武昌太守”的条文。 这个一“删”一“增”,首先说明古人特别是古代的史学界对“陶渊明为哪里人”是有争论的。其次也说明房玄龄等在陶渊明究竟为何人的问题上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个成果足可以否定沈约等关于“浔阳柴桑人也”的说法,只是这个成果还没有达到可以断然肯定陶渊明故里具体位置的高度而已。房玄龄等奉皇命集体编写《晋书》,能在典籍中敢于对前人所说做出“增删”决定,决不可能是草率行为,肯定是深思熟虑,有理有据。 这就告诉我们,《晋书》陶传虽然没有明确记载陶渊明到底何方人氏,但有那个“祖茂,武昌太守”的记载,至少也为人们寻找陶渊明为哪里人的答案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有人说,沈约写《宋书》的时期离陶渊明时代近,而房玄龄他们则离陶的时代远,应当采信沈约的。这种以“先来后到”为准的说法,似有道理,但沈约著《宋书》毕竟是个人所为,而房玄龄等作《晋书》乃集体行为,我们在没有充分证据指出后者错误时,“集体”的智慧也不失为一种重要参考。 2.千年史链,“始家宜丰” 在我国史界,有一条明确记述陶渊明故里的千年史链,那就是“始家宜丰”。值得所有陶研者注意的是,在房玄龄之后,我国史学界还围绕着陶渊明的故里问题,形成了一条共识达千年之久的史链。那就是陶渊明“始家宜丰”。 北宋朝廷史官乐史载《太平寰宇记》卷百六载:“渊明故里,《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用新发现的史料对沈约说法进行了纠正,并对《晋书》的陶传进行了补正。 南宋史学家王象之著《舆地纪胜》,在其卷二七把乐史的记载说得更为清楚:“《图经》载,渊明家宜丰县东20里,后起为江州祭酒,徙家柴桑,暮年复居故里”,并列举了故里的遗迹,遗址就在“延禧观之七里山”。 非常巧合的是,《舆地纪胜》所引《图经》这个诗人一生行止的记载,正与上述我们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出的内证几乎一致。 后来的《元一统志》卷九,不仅同样确认了《图经》的史料,而且还给陶渊明重新立传,开创国志为陶渊明立传的先河。到了明清两朝,其《一统志》也都认可上述史实。 可见,从房玄龄及其《晋书》始,已经形成了一条为陶渊明里籍正本清源的千年史链。 非常遗憾的是,在我国史学界和文学界,自明朝江西李梦阳在九江地区弄出个“断碑”之后,事情便发生了逆转。尤其是清代的王谟在《江西考古录》断言“陶渊明行止始终不离柴桑”之后,人们连“直面”上述史链的勇气也没有了。于是,种种质疑应运而生。有人说,“《图经》已佚,原始证据难寻,不可轻信这种史料”;还有人说,《太平寰宇记》是“稗史”,等等。凡读过《太平寰宇记》的人都会知道,它引载《图经》不仅非只一例,而且引用的“图经”种类也很多,县、郡、州的图经都有。显然,那个记载渊明故里的没加任何限制语的《图经》,应当是全国性的,相当于后来的《一统志》。《太平寰宇记》广引《图经》的事实本身说明,《图经》在历史上确有。而且,《舆地纪胜》、《元一统志》的作者也证实了《图经》确有“渊明始家宜丰”的记载。  五、陶渊明“旧居”在曾属上京的宜丰 事实上,众多史料证明,“渊明始家宜丰”的千年史链,经得起反复推敲。 我们且不说前文提到的国志以及《江西通志》、《瑞州府志》、《宜丰县志》、《新昌县志》、《上高县志》有相关记载,也不说江西、湖南、安徽、浙江四省13部《陶氏族谱》均载陶渊明的始家之地(或少长之地)在宜丰义钧乡七里山,众口一词,还不说宜丰七里山发现有陶渊明故里种种遗迹,只要仔细看看陶渊明本人所写的《还旧居》,就可从中推断出“渊明始家宜丰”的记载一点都不假。 1.“还旧居”乃“归园田居” 所谓“旧居”,从前居住过的住所。陶渊明的“旧居”是指什么呢?翻开《陶渊明集》,我们必定会发现,“旧居”一词,在现存陶渊明诗文中只使用过两次。一次是本诗以“还旧居”为题;另一次是《拟古》,“其三”有“翩翩新飞燕”,“相将还旧居”。从《拟古》所有九首诗词的文意来看,它应为诗人晚年回归“园田居”的作品。所谓“翩翩新飞燕”,可与“命室携童弱”与“始室丧其偏”等诗句连起来,推断为作者隐喻从未来过“园田居”的后娶妻子和幼子。“相将还旧居”,就是诗人在晚年带着这两个“新燕”回到了“园田居”。由此可见,诗人以《拟古》中的“还旧居”为题写作本诗,既说明本诗与《拟古》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也说明“旧居”这个地方就是诗人别后30年带着“新燕”归来的“园田居”。 同时,诗人在“归园田居”其四,专门描写了一个“试携子侄辈”上山祭拜父母坟墓的场面。这就告诉我们,诗人笔下的“旧居”,既是“园田居”的代名词,也是他父母的居所,是他晚年朝思暮想的休养生息之地。 2.“旧居”在原属上高管辖的宜丰境内 《还旧居》开篇说“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而还”,这里的“上京”所指何地,我们借助“训诂”,便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从字意上解释,“京者,高也。”《辞海》、《辞源》上解释“京”的本意是“高”。《三国志》中公孙瓒“筑京抗曹”的“京”是“高台”的意思,萧统《陶渊明集序》中“莫之与京”的“京”是“高明”的意思,京城里的“京”也是“高”的意思。这就告诉我们,在陶渊明笔下,“上京”,很有可能就是“上高”的通假或者假托。 “上京”,即上高,“旧居”即“园田居”,在原属上高管辖的宜丰境内。 在《陶集》中,诗人有两处使用过“上京”一词,一处是《答庞参军》中的“作使上京”,一处是《还旧居》中的“畴昔家上京”。 在过去的传统解释中,人们讲《答庞参军》中的“上京”是对京城的尊称,而还旧居的“上京”,则是指九江某地的玉京山,这本身就不能成立。在诗人笔下的这两个“上京”,应当是同一意义,而不可能是有异议的两个不同地名。同时,“上京”也不是对东晋首都建康的尊称。因为称首都为“上京”者,一般是附属国对宗主国而言,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而且,如果上京是指首都建康,那诗人的“旧居”就应在如今的南京,可目前绝无这方面的任何史料,显然不可取。 查上高县沿革史料可知,三国孙吴时立县,因居民多为河南上蔡(春秋时期的蔡国京城)移民,名曰“上蔡”;后考虑到与河南上蔡同名,东晋太元年间也就是诗人读书的“少时”曾改为“望蔡”;几经变迁至唐初,望蔡并入建城(高安),唐中和中才立“上高”。《太平寰宇记》载:“上高县,本高安之上高镇,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这些记载和解释,可以使“上京”通假“上高”的意思成立。 那“上京”通假“上高”,又与“始家宜丰”何干呢? 通过查阅史料可知,宜丰是三国孙吴时期才从“建成”(今高安)分立出来的一个县,开始叫“宜丰”,后来几度变迁,曾经分属于“上蔡(上高)”、“阳乐(万载)”、“望蔡(上高)”等地,直到唐中和中,才重新单独立县,名曰“新昌”,于近代才恢复“宜丰”的古名。 《太平寰宇记》载:“阳乐县城在(筠)州西北八十里义均(当为钧)乡,吴大帝时始于上蔡县管”。这个义钧乡(今宜丰秀溪英塘一带),就是七里山的所在地,即《舆地纪胜》所说的陶渊明故里。故翻查《上高县志》,其同治版也有陶渊明故里在义钧乡的记载。 所以,“上京”通假“上高”,宜丰曾属上高,是有史可循的合理推断。特别是《还旧居》“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中那个“六载”的时间概念,更是可印证“始家宜丰”的真实性。 “六载”是前句“家”的补语,“去”与“归”并列。全句应当理解为:在上京住了六年,离开后又回来了”,不能理解为“离开(上京)六年后又回来了”。 把这个“六载去还归”,与宜丰所发现的《秀溪陶氏族谱》(宣统三年版)记载相联系,经得起反复推敲。该谱说,陶渊明26岁(太元十五年)在南山“构庐居焉”。也就是说,在秀溪这个地方,既有陶渊明父母居住的房子,即“旧居”,也有属于陶渊明自己的居所。从现有史料所显的时间去推算,陶渊明在秀溪这个地方的父母之居,恰好是不多不少整“六年”。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陶渊明父母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原因来到秀溪,也不知道陶渊明小时候跟不跟父母一起居住,但有如下事实却可以肯定:**,陶渊明“少怀高趣”、“委怀在琴书”,少年时代必定会在外求学,无论宜丰还是“安城”这种地方,都不可能造就如此一个大知识分子。第二,陶渊明在20岁那年,即公元384年、太元9年,“弱冠逢世阻”,父亲死了,他无论在哪都必须回乡“守制”,肯定要住在父母的居所。这样,“太元十五年”在南山构庐的家谱记载,正好可以推算出陶渊明在“旧居”住了“六年”时间。 通过以上这些史料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论定,诗人笔下的“上京”,就是“上高”,它就在曾经属于上高县管辖的宜丰义钧乡。 这样看来,“渊明始家宜丰”可以说是国史有叙,诗人有记,家谱有载,几者之间互相印证了。 3.“上京”乃“上高”,在陶诗中的佐证 《答庞参军》的“作使上京”,若按照“上京”就是“上高”的理解,那庞参军的“作使上京”,就应当是庞遵庞通之庞参军这个人作为朝廷的使者来过“上高”,而且是在诗人归来宜丰“旧居”以后作为“使者”来的,这完全可能。 沈约《陶传》,载有一个诗人义熙末被征著作佐郎的史实,而且也载有一个江州刺史王弘“令潜故人庞通之”具酒“邀之”的故事,其它《陶传》对此都无异议。“义熙”,是东晋王朝的最后年号;“义熙末”,即公元419年。这个时候,刘裕代晋已成事实,诗人年纪在56岁左右,刘裕要征召诗人出山做官,正当时也。而且,陶传中“征著作佐郎”以及王弘“令”庞通之邀酒这些史实后面隐藏的事情必定是,朝廷的征命需要有人传达,庞遵的“半道邀之”也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正好是庞通之“作使上京”的正解。 在陶集中还收录有三篇诗人与庞遵对话的诗词,篇篇都有关于“著作郎征命”的内容。一篇《答庞参军并序》写有“大藩有命、作使上京”的字样,明显包含着“大藩”王弘甚至是刘裕命庞遵“邀之”的史实;另一篇《答庞参军并序》说“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讲自己闲散已久、纸笔不听使唤、会犯错误,明显是不愿在新朝做文字官员的推托之辞;《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吁嗟身后名,于我为浮烟”,更是点明了自己对“青史留名”的鲜明态度。如果把这几篇作品连串起来,一个庞遵受命传达朝廷征命被诗人婉辞拒绝的画面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通过查史可知,王弘是刘宋始皇刘裕的肱股和托孤大臣,在422年以前任江州刺史;陶渊明的“鲂鲤跃麟于将夕”(见《游斜川》)事发在“辛酉(丑)年”,即421年,他给庞遵的几篇诗词也作于这一年前后,他的《于王抚军座送客》中所叙情事,同样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在相关年有相关人说相关话做相关事,可见刘裕对诗人的征命是委托给王弘、王弘再命庞遵具体执行的。因此,庞遵“作使上京”的史实完全可以为“上京”托指“上高”提供足够的理由。 综上所述,把“上京”理解为“上高”,不仅可以解决诗人“旧居”的具体地理位置问题,佐证《图经》记载和千年史链的真实性,而且还可以正确解释《陶渊明集》中的诗篇,正确解释隐居多年的陶渊明何以会在晚年仍然还同朝廷要员打交道的疑惑。 
必须正视的是,确认“始家宜丰”一说,只能说明陶渊明的父母曾经在宜丰这个地方居住过,陶渊明有“入仕”前在宜丰居住即“始家宜丰”的经历,还有一段“晚年回归”宜丰的历史。 但我们不能由此臆断陶渊明就生在宜丰长在宜丰,陶渊明的故里只在宜丰。而且,“始家宜丰”一说看似与“柴桑人”一说对立,其实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因为它并不否定柴桑具有渊明文化遗迹遗址的史实,也不妨碍柴桑作为“浔阳陶”发祥地的荣誉,只是还了陶渊明丰富人生的本来面目,比较全面而且真实地描绘了陶渊明的一生行止。 就学术层面而言,持“柴桑”一说的专家学者,应本着对自己对别人对中华文化负责的姿态,努力寻找渊明行止的真实轨迹,这样更利于正确地理解陶渊明本人及其诗文,还陶渊明以本来面目。
|